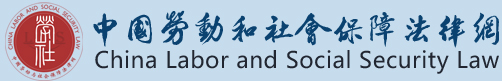我看“孙志刚”案
刘昕杰(四川大学法学院)
27岁的农村大学生因为在一项本身就不合理的遣送制度中想维护自己的一点权利竟被毒打致死。这不仅是孙志刚家庭的悲哀,也是这个社会的悲哀。从中表现出来的是我们在进行制度建设中对人的权利、生命权利的态度。
遣送制度的不合理其实并不难为管理者理解,之所以能够存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唯一的理由是这一制度能够避免外来人口的无序进入,维护当地社会的稳定,保障经济的发展。
诚然,稳定压倒一切,在经历了长久的社会动荡之后,我们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进行经济建设,发展才是硬道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很落后,经济发展一旦停滞会带来诸如就业问题等社会影响。但需要强调的是。稳定和发展并非我们工作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们物质精神的要求。因此,稳定不代表压抑个人权利,发展不意味单纯追求GDP数字的增长,我们需要的稳定和发展是在充分尊重个人权利基础上的稳定和发展。稳定是指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胜利地行使自己的权利。通过公民张扬个性,崇尚自由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是经济的发展,也更是个人权利空间的不断扩展。在这样的社会里,就像罗伯斯庇尔所描述的“祖国保证每一个人的幸福,而每一个人为祖国的繁荣和共荣而自豪”。
一旦制度的建构忽略对公民权利的尊重,这项制度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合理性,而如果这项制度要以牺牲公民生命为代价的话,那无异于在向世人倡导这样一个观念:可以漠视你同类的生命。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最可宝贵的是生命,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我们在关注伊拉克战争时,对美国的炮弹击中伊拉克平民造成的伤亡而忿忿不平,但却对自己同胞被和平的制度机器剥夺生命反应冷漠。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肯定制度正确的前提下寻找个人的责任,寻找自己的责任。孙志刚死后,靠一亩三分地供养他读完大学的老父亲没有责备那些“执法人员”,而是反悔自己让儿子读了大学。他认为是读了大学让儿子太认“死理”,如果让儿子一辈子呆在农村种地,就不会“招惹是非”,哀莫大于心死啊!难道我们的制度就只能是建立在老实本分、逆来顺受,世界上最善良的农民身上么?
孙志刚是幸运的,他的死震动了媒体,当事人也被追究了责任,多少给死去的他一些抚慰。但还有那些许许多多没有被报道的生命呢?我只有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德国神父马丁的忏悔:“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没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没说话;然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没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这个时候,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我为孙志刚的死而痛心。因为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结构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孙志刚,如果不从制度层面重新审视我们对待个人权利态度的话,下一个孙志刚也只有束手待毙。
是应该彻底反省了。
新闻动态
News网站公告
Notices- 2023-01-10 公告 | 2022年度中国社会法十大影响力事例发布会
- 2022-12-29 2022年度中国社会法十大影响力事例评选
- 2022-01-31 新年贺词|林嘉:砥砺深耕,履践致远
热点话题
Hot topic- 2017-09-15 [公告]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论坛第28讲:劳动法的法经 济学分析
- 2017-09-15 “变革与发展: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劳动法治建设”国际 研讨会